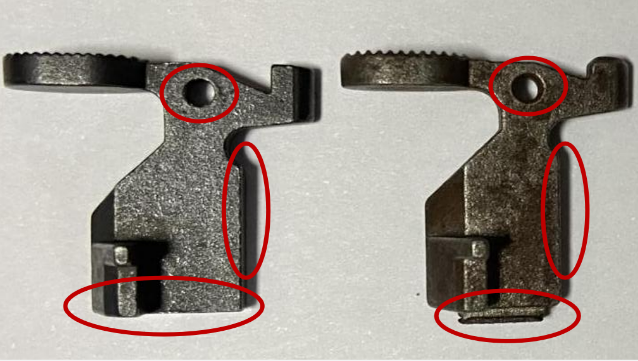【内容提要】澳门开埠400余年,中西文化相互交融,共同促成了澳门服刑人员未成年子女救助两大理念权利平等”、“国家亲权”。这两大理念贯穿于澳门《民法典》、《家庭政策纲要法》等法律法规法令中,并推动形成了澳门独特的服刑人员未成年子女救助主体与内容。借鉴澳门服刑人员未成年子女救助经验,对推动和促进我国内地服刑人员未成年子女救助工作,具有重要意义。
【关键词】澳门服刑人员未成年子女救助权利平等国家亲权
探讨澳门服刑人员未成年子女救助,对于更加深入地了解澳门司法与社会救助,更好地总结澳门在服刑人员未成年子女救助方面的经验,并以此促进和推动内地服刑人员未成年子女救助工作,具有重要意义。
一、澳门服刑人员未成年人子女救助理念
澳门开埠400余年,中西文化交融共存,各种服刑人员未成年子女救助理念长期共存、和谐相处。华人社会传统的“幼吾幼以及人之幼”{1}及“慈幼”、“幼有所长”{2}观点,佛教宣扬的“普度众生、众生平等”思想,基督教和天主教主张的“爱人如己”博爱观等,共同促成了澳门服刑人员未成年人子女救助两大核心理念权利平等”、“国家亲权”。“权利平等”,是指“每一个服刑人员未成年子女均有权享有被照顾、协助和保护的权利,不因其父母或法定监护人的过错与身份特征而遭受一切形式的歧视或惩罚。”[1]国家亲权”,又称“终极父母”、“国家父母”,是指“作为主权者,国家应竭尽所能向无法照管自身的公民提供保护”,{3}本文中,它特指由于父母或法定监护人处于服刑状态而导致其未成年子女在事实上处于缺乏照管与监护状态的,澳门政府应当承担起“家长”的责任,向这些未成年子女提供必要的照顾与保护。
二、澳门服刑人员未成年人子女救助法律渊源
澳门没有专门的“服刑人员未成年子女救助”法律法规或者法令,相关规定主要散见于澳门《民法典》、《家庭政策纲要法》、《剥夺自由处分之执行制度》、《重组澳门社会工作司,将预防及治疗药物依赖办公室纳入其中——若干废止》(以下简称《重组澳门社会工作司》)以及澳门签署通过的联合国《儿童权利公约》之中。[2]上述法律法规法令及国际条约,虽规定分散,但却互为补充,共同构成了澳门服刑人员未成年子女救助体系框架。
澳门《民法典》首先明确了未成年人的范围,即18周岁以下的任何人,[3]其次以专章节的形式,详细规定了“在事实上丧失亲权监护”的(诸如服刑人员未成年人子女)各种救助措施;《家庭政策纲要法》主要规定了行政当局在保护服刑人员未成年子女方面的义务;《剥夺自由处分之执行制度》主要针对女囚犯3岁以下未成年子女规定了一系列救助措施;《重组澳门社会工作司》明确了澳门社会工作司乃社会援助的官方工作机构,而特殊家庭(如服刑人员家庭)之未成年人子女正是其重点援助的对象之一;联合国《儿童权利公约》主要从原则上指明了“服刑人员未成年子女”享有同其他任何未成年人同等的被照料和协助权利。
三、澳门服刑人员未成年子女救助主体
(一)澳门服刑人员未成年子女救助官方主体
根据《重组澳门社会工作司》法令的规定,澳门服刑人员未成年子女救助的官方主体为社会工作司(现改名为社会工作局)。社会工作局主要是通过提供经济、物质援助以及个案辅导等工作,来帮助问题家庭及青少年(如服刑人员家庭及其未成年子女)。而这一救助责任主要分配在社会工作局下属的家庭暨社区服务厅和社会互助厅两个部门。家庭暨社区服务厅,主要是向家庭及个人提供庇护,如,对由于父母处于服刑状态而导致的未成年人所处家庭经济困难的,提供必要的资金、物质援助以助其摆脱困境。家庭暨社区服务厅具体服务工作,主要是通过分布在澳门各个区的社会工作中心和家庭辅导办公室来落实。社会互助厅内部专设儿童暨青年服务处,来负责对未成年人的帮扶和救助,并为家庭援助工作提供必要的合作等。例如,为需受援助的服刑人员未成年子女开展评估并制定帮扶方案和计划,等等。[4]这样一个分工明确又相互配合的救助主体机构(详见图一),确保了服刑人员未成年子女能得到及时以及切实的照顾与扶助。
(图略)
图一:澳门社会工作局部分机构设置图
(二)澳门服刑人员未成年子女救助的非政府组织
非政府组织(英文缩写NGO),联合国新闻部将其界定为“非营利性的公民自愿组织,它们提供各种各样的服务和发挥人道主义作用。”澳门政府历来重视发挥社会力量,推动及资助非营利民间志愿机构协助主理救助服务,以最大化救助诸如服刑人员未成年人子女之类的特殊家庭及群体。负责这一工作的官方部门是澳门社会工作局,该局“以签订合作协议及进行培训活动等方式,向这些私立的社会互助机构提供技术、财政、物质援助等”。[5]技术援助,是指协助制定、组织开展活动并进行评估,对人员进行培训、提供相关的资料文件等;财政援助,主要包括分担部分社团日常运作费用(如人员及装备费用)、投资开支及开展活动之经费;物质援助,主要是指设施、设备或物料的给予。[6]如,澳门社会工作局就代表澳门政府对天主教澳门教区属下的社会福利志愿团体、澳门街坊会联合总会家庭服务中心给予财力等方面的资助。[7]
四、澳门服刑人员未成年子女救助内容
对于身处不同困境的服刑人员未成年子女,澳门设置了详尽的救助措施,确保他们能够及时地获得所需的经济、物质、精神乃至新监护人的救助。
(一)事实单亲家庭救济
对因父母或法定监护人一方正在服刑而导致未成年子女事实上处于单亲家庭状态的,政府将给予一定的经济、物质以及计划辅导等特殊救助。如,在行政当局鼓励和支持下成立的家庭辅助中心,将根据单亲囚犯家庭的困难与需求为其提供特别的辅助工作,如经济、物质援助等,[8]而儿童暨青年服务处也会根据需要提供相应的配合工作。
(二)事实孤儿救济
对因父母或法定监护人正在服刑而导致未成年子女事实上处于孤儿状态的,澳门政府充分发挥其“国家父母”的职责,设置了一系列的弥补亲权监护措施。第一,及时报告制度。当父母亲权的行使在事实上受阻时(如父母被逮捕或在监狱服刑),在工作期间获悉该情况的任何行政当局、司法当局或负责民事登记的公务人员,都应当履行告知义务,及时将该情况告知有管辖权的法院,获悉该情况的检察机关应当立即采取能够保护该未成年人的必要紧急措施,法院应当依职权促使设立对该未成年人的监护制度。第二,强制监护制度。父母亲权的行使在事实上受阻达到6个月以上的,必须对未成年人进行监护,监护职责的行使人(以下简称监护人)由未成年人的父母指定并经法院确认,或者由有权法院直接进行指定,被指定的监护人,若无法定阻却事由(如,需照顾两名以上的直系血亲卑亲属或者本人年龄已经超过65岁的老者),不得推辞监护职务。第三,监督监护人制度。为确保对未成年人监护的零空缺,一方面,必须在未成年人亲属中甄选出一名与原监护人不同血亲亲系的“监督监护人”与监护人一起履行对未成年人的监护责任,并在未成年人与监护人发生利益冲突时,维护未成年人的合法权益;另一方面,原管辖权法院应当有权对监护人的监护权行使监督,监护人应根据法院要求或在其职能终止时,向法院提交监护报告。法院若发现监护人未履行监护职责或欠缺履行职责能力,则将撤销监护人的资格甚至给予一定的惩罚。第四,交托相关机构监护制度。对于无法找到符合条件的监护人来履行监护职责的,服刑人员未成年子女则将会被送至适合的公共或者私人机构,由该机构的主要责任人承担监护人的职能。[9]
(三)亲情沟通、亲职辅导
为维系和保障未成年子女与服刑父母间的情感沟通,未成年子女可以定期与服刑的父母见面交流。根据澳门《路环监狱规章》第16条第4款规定,除直系血亲卑亲属或兄弟姐妹外,16周岁以下未成年人不被允许探视服刑人员。[10]实践中,澳门监狱还将这一规定进行了最大化落实,以尽量满足未成年子女与其服刑父母的情感交流,即有16周岁及以下未成年子女的服刑父母,可以申请参加儿童援助计划,每周日与其未成年子女会面,通过游戏的方式拉近父母与子女间的关系。监狱还允许安排专门的社工人员从旁进行相关的亲职辅导,如,帮助父母与子女进行有效的语言沟通与行为互动等,以确保会见的积极效果,更从2010年起,澳门监狱坚持每年举办一次“六一节亲子活动”,使服刑人员未成年子女在儿童节也能够与父母团聚、同享游戏与欢乐。
(四)特殊照抚
对于女囚犯3岁以下子女规定了特别保护内容。一是女囚在监狱产子后,对该婴儿进行出生登记时,应当隐去其出生地、母亲囚犯身份等能反映出该婴儿与监狱关系的身份资料;[11]二是女囚犯3岁以下的子女,根据最有利于未成年人利益原则,可允许该幼童跟随母亲在监狱生活直至其满3岁;三是当3岁以下幼童随母在监狱生活时,在不违反监狱内部规章及有关条件的前提下,应确保女囚犯与其子女每日共同生活在一起。
五、澳门服刑人员未成年人子女救助之借鉴
(一)完善未成年人法律保护体系,增强其可操作性
当前我国许多法律法规中都或多或少、直接间接规定有服刑人员未成年子女保护与救助的内容,如《中华人民共和国未成年人保护法》、《中华人民共和国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以下简称《民法通则》)、《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以下简称《监狱法》)等等,但这些规定过于原则化,且缺乏监督、惩罚措施,可操作性不强。如《监狱法》第19条规定:“罪犯不得携带子女在监狱内服刑”,但对于正在服刑的罪犯,由谁承担照顾、监护他们的未成年子女却没有规定。故建议对上述法律法规给予细化完善,并增加监督惩罚措施,增强其可操作性。以《民法通则》为例,可在《民法通则》第二章“监护”一节中,明确对服刑人员未成年子女(事实孤儿)进行监护的强制性,细化监护人选择的法定条件、监护责任与义务、对监护人的监督与罢免,相关惩罚措施等等。再如,可将“服刑人员可每周定期会见其未成年子女一次”纳入《监狱法》的“会见”规定当中,以增进未成年子女与其服刑父母间的亲情联系。
(二)明确政府救助主体和职责分工,确保救助实现“无缝对接”
首先,明确服刑人员未成年子女救助的政府主体是民政部门。今年国务院新颁布的《社会救助暂行办法》(以下简称《办法》)于2014年5月1日起正式实施。根据该《办法》的规定,“民政、卫生计生、教育、住房城乡建设、人力资源社会保障等部门统称社会救助部门,而国务院民政部门负责统筹社会救助体系建设”,[12]那么将服刑人员未成年子女救助主体明确为民政部门的职责范围,应当是最合适不过的了。其次,发挥民政部门现有机构职能优势,明确职能分工,将服刑人员未成年子女救助落到实处。以市一级民政局为例,该部门内设的社会事务与社会福利科,负责承担孤儿的权益保护等工作,那么对于处于事实孤儿的服刑人员未成年子女权益保护工作建议可由该科负责;内设的社会救助科,负责组织实施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医疗救助、临时救助等工作,故建议该科可承担对服刑人员未成年子女的最低生活保障、医疗救助、临时救助等工作;直属单位社会救助管理站,实行365天24小时不间断值班制,负责对所辖区内生活无着的流浪乞讨人员实行救助、为不同类型受助对象提供心理咨询、情绪疏导等专业社会工作服务并以强制性手段对流浪、乞讨儿童进行救助、保护、教育等等,因此,服刑人员未成年子女具体的保护、教育以及心理辅导等工作建议由该机构承担。[13]最后,充分发挥民政部门统筹社会救助体系优势,协调教育、卫生、公安、检察院、法院、监狱以及团委、妇联等部门或团体,以联席座谈会议、联合签署文件、联合开展配套活动等方式方法,为服刑人员未成年子女救助提供一个全方位的社会保障机制,确保救助实现“无缝对接”。
(三)推动及资助民间志愿机构,协助开展社会救助工作
对于民间志愿组织,政府的推动、支持是至关重要的。但目前政府给予服刑人员未成年子女的民间志愿救助机构的关注与支持十分有限,以致这些机构的运转大都依赖于社会捐助、自办产业、自给自足等方式来维持。由于资金来源的不稳定性和短缺性,造成很多救助机构长期面临严峻的经济压力,举步维艰,很多被救助的服刑人员未成年子女生活水平和质量偏低,而医疗保健、心理辅导等措施更是难以得到有效保障。因此,当前亟待政府部门加大财力、物力支持,鼓励并推动这些民间志愿组织的发展,以保障寄居在此的未成年人能有一个较稳定、舒适的生活环境,从而健康、茁壮成长。
(四)细化救助内容,确保服刑人员未成年子女救助“零空白”
一是根据服刑人员未成年子女的生活状况和亲子关系,给予服刑人员未成年子女家庭及个人相应的经济支援、心理辅导以及亲职教育等。二是对于事实上处于孤儿状态的服刑人员未成年子女,政府应当承担起“国家父母”的职责,一方面要求民政部门、公安、检察院、法院以及司法部门等在履行职务过程中发现上述情况时,要承担及时告知义务;另一方面要及时为该“事实孤儿”指定合适的监护人或将其送至适当的救助机构给予照顾和保护,并加强对指定监护人或指定机构的监督与管理。三是促进服刑人员与其未成年子女间的情感交流与维系。除定期安排服刑人员与其未成年子女会见外,还应在节假日和特殊日期(如未成年子女生日等)安排一些节目或活动,促进未成年人与其父母节日的共享与交流,甚至监狱可设立亲子房,在确保安全的情况下,允许服刑人员与其子女短暂同住。四是对特殊群体的照顾。对于处于哺乳期的女囚犯,在确实更有利于未成年人的情况下,可适当考虑允许其一周岁以下幼童随母生活。
【注释与参考文献】
[1]参见澳门签署通过的联合国《儿童权利公约》、《澳门民法典》、澳门《家庭政策纲要法》等。
[2]本文中,涉及上述澳门法律法规法令的资料均来源于澳门政府网澳门法律网,
[3]参见《澳门民法典》第111条的规定。
[4]参见《重组澳门社会工作司,将预防及治疗药物依赖办公室纳入其中——若干废止》第4条、第12至第20条之规定。
[5]参见《重组澳门社会工作司,将预防及治疗药物依赖办公室纳入其中一若干废止》第4条第10款的规定。
[6]参见澳门《订立社会工作司对从事社会援助活动之私人实体之援助形式》的规定,来源澳门政府网——社会工作局:常用法规。
[7]澳门政府网——澳门社工局:财政资助名单。
[8]参见澳门《家庭政策纲要法》第12条的规定。
[9]参见《澳门民法典》第三编第二章第三节“弥补亲权之方法”之规定(即《澳门民法典》第1778条至第1824条,共计47条)。
[10]来源于澳门监狱网——常用法律:《核准路环监狱规章》。
[11]参见澳门《剥夺自由处分之执行制度》第84条。
[12]参见《社会救助暂行办法》第3条至第5条之规定。
[13]参见珠海市民政局官网——机构职能。
{1}鲁国尧.孟子注评[M].南京:凤凰出版社,2006.10.
{2}{3}张鸿巍.儿童福利法论[M].北京:中国民主法制出版社,2012.47.88.
{4}胡俊军.法治背景下我国非政府组织的发展[D].华东政法大学硕士论文,2010.2.
作者:郭瑞霞
来源:《山东警察学院学报》2014年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