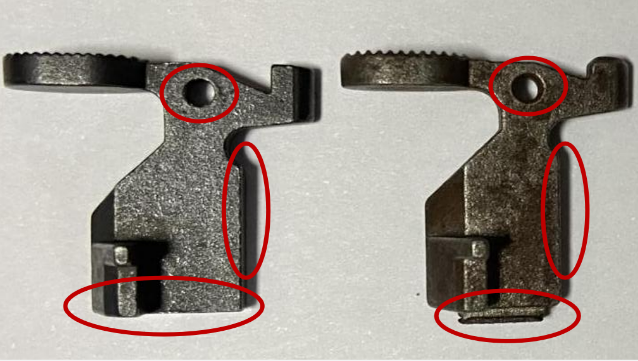刑诉法专章中确立的附条件不起诉制度,不但为践行对犯罪的未成年人实行教育、感化、挽救的方针提供了一种具有弹性和柔性的非罪化处理机制,而且为刑事诉讼程序中检察官起诉裁量权的运用以及司法分流提供了新的渠道。但从司法实践来看,适用的情况并不理想。例如,如何理解附条件不起诉与酌定不起诉的区别,怎样划分两者适用的案件范围;如何设置附条件不起诉合理的考验期限等都不甚明了。笔者认为,考虑到附条件不起诉制度未来可能扩展至成年人案件,有必要对这一基本理论问题予以厘清。应将附带处分作为附条件不起诉的核心要素来理解。
所谓附带处分,是指检察官在决定附条件不起诉的同时,要求被不起诉人在一定期间内完成某些事项,被不起诉人只有完整履行这些附带处分,才能在附条件不起诉考验期限届满时获得最终的不起诉决定,也可以称之为“附随处分”或“附带条件”。附带处分不同于考验期限内的基本行为规范,因为后者是对所有被附条件不起诉人的统一要求,而附带处分则可以根据人和案件的具体情况来设定。此外,附带处分的履行期间等于或短于检察机关确定的考验期限,而考验期限内的基本行为规范的执行期间则等同于考验期限。刑诉法第272条第3款规定,被附条件不起诉人应当遵守下列规定:遵守法律法规,服从监督;按照考察机关的规定报告自己的活动情况;离开所居住的市、县或者迁居,应当报经考察机关批准;按照考察机关的要求接受矫治和教育。其中前三项即属于考验期限内的基本行为规范,最后一项属于附带处分,但语焉不详。《人民检察院刑事诉讼规则(试行)》第498条对此作了细化,规定了下列六项附带处分:完成戒瘾治疗、心理辅导或者其他适当的处遇措施;向社区或者公益团体提供公益劳动;不得进入特定场所,与特定的人员会见或者通信,从事特定的活动;向被害人赔偿损失、赔礼道歉等;接受相关教育;遵守其他保护被害人安全以及预防再犯的禁止性规定。
之所以将附带处分视为附条件不起诉的核心要素,理由如下:
一方面,附条件不起诉源自检察官起诉裁量权的扩充与发展。检察官的起诉裁量权随着起诉便宜主义对起诉法定主义的合理修正而产生,并随着犯罪形态的多样化和复杂化不断发展。与之相对应,公诉权早已从最初单纯的司法请求权发展到准司法处置权。按照日本学者的观点,检察官的起诉裁量权经历了从“微罪不诉”到“起诉保留”再到“起诉犹豫附保护观察”的不同阶段,而“起诉犹豫附保护观察”就是对应附条件不起诉这种既设定考验期限又附有附带处分的不起诉制度。可见,附带处分的出现使检察官的起诉裁量权从初级和中级阶段跃升至高级阶段,从而使检察官在运用起诉裁量权时不但要完成“是”与“否”的“判断题”,还需完成更为复杂的“多项选择题”,从一系列选项中择定对涉案人及社会最为适宜的附带处分。附带处分是检察官践行更为高级的起诉裁量权,以应对更为复杂多样的犯罪形态和社会情境的关键之所在。
另一方面,附条件不起诉还体现了侧重于特殊预防并兼顾一般预防的综合预防理论。附条件不起诉作为审前司法分流的重要方式,特别预防理论对其产生与适用具有支配性地位。相较而言,要求被附条件不起诉人在考验期限内遵守最基本的行为规范对实现特殊预防助益有限,特殊预防目的的实现主要仰赖于针对个人的犯因性需求并具有个性化的附带处分。同时,附带处分也有助于实现一般预防的目的。考验期限内被附条件不起诉人遵守基本的行为规范,这一要求接近于每个守法公民的基本义务,而不具有让其为自己已经实施的不当行为付出相应代价的意蕴。而附带处分所涵括的公益劳动、向被害人赔偿损失与赔礼道歉以及接受相应教育与治疗等内容则以刑罚之外的方式让被附条件不起诉人为其之前的不当行为付出了相应的代价。从实现综合预防目的的角度,附带处分在附条件不起诉中的核心地位是不容置疑的。
台湾地区多年缓起诉的实践也为附带处分的核心地位提供了实证注脚。在台湾地区刚确立缓起诉制度的2002年,不附加任何附带处分的缓起诉人数占全部缓起诉人数的72.1%,因而被认为有“宽滥之虞”。而随着实践经验的积累,检察官逐渐认识到附带处分之于缓起诉的核心地位及相应配套机制的完备,缓起诉的数量大幅减少,仅适用于个别的案件。
事实上,正是附带处分的存在使附条件不起诉区别于单纯的推迟起诉或暂缓起诉,这一点从附条件不起诉的名称上即可获知。正确认识附带处分在附条件不起诉中的核心地位对于合理运用附条件不起诉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前文所谈到的实践中存在的问题也都可以借此给出一个解答:如何界分酌定不起诉与附条件不起诉适用的案件范围,不应该仅仅依据“不需要判处刑罚或者免除刑罚”和“可能判处一年有期徒刑以下刑罚”这一量刑上的区别,同时还应从综合预防的角度考虑是否需要及如何施以附带处分;而如何合理设定附条件不起诉的考验期限,则需要考虑履行各种附带处分的情形,刑诉法之所以规定了6个月至1年的考验期限,正是为了能够包容多样化的附带处分。更重要的是,只有明确附带处分的核心地位,才能使附条件不起诉在未成年人案件中得到充分的运用,培育相应配套的社会支持机制,并最终扩展至成年人案件。
作者:何 挺(北京师范大学刑事法律科学研究院副教授)
来源:检察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