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刑辩痴人刘平凡律师网 日期:2024/3/31 10:29:44 浏览:114
引言
2012年9月13日,北京市一中院开庭审理了郭某等四人涉嫌贩卖毒品一案。被告人郭某当庭提出自己在供述前遭侦查人员威胁,其辩护人申请法庭启动非法证据排除程序。法庭批准该申请,启动了非法证据排除程序,并依法传唤两名当事警察出庭作证,对郭某做出的五份有罪供述的合法性进行审查。最后,法庭以公诉人出示的证据不够确实充分,不能排除侦查人员对郭某的讯问存在违法行为以及讯问过程没有同步录音录像为由,排除了郭某作出的第一份有罪供述。但是,其余四份有罪供述未予排除。该案审判长就此解释道:被告人和辩护人当庭提出,第一次受到侦查人员威胁后就有了心理阴影,但是辩方没有拿出证据来证明阴影真实存在。此外,控方出示的证据中,后面四份有罪供述都有同步的录音录像,证据扎实,所以只排除第一份有罪供述。最终,北京市一中院认定被告人郭某贩卖毒品罪成立,对其判处无期徒刑。[1]由此,“北京非法证据排除第一案”在法院做出排除侦查人员非法获取的第一份被告人供述后,仍根据包括之后的讯问所获取的四份有罪供述在内的其他证据对被告人作出了有罪判决。
就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适用而言,该案无疑具有示范意义。但该案同时也带来一系列问题:侦查人员使用非法讯问方法获取了被告人的第一次供述,后来,侦查人员没有再使用非法讯问方法,但被告人做出了重复的供述。此时,法院排除第一次获取的非法供述并无争议,但应否排除之后的重复供述呢?先前非法讯问方法对后来被告人重复的供述是否产生影响,应当如何判断这种影响?先前非法讯问方法对被告人所造成的影响在之后的讯问中是否有消除的证明责任,应由哪一方承担?应采何种证明标准?总之,我们应当如何应对“重复供述”所产生的问题?
重复供述,是指侦查人员在采用刑讯逼供等非法方法获取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供述后,在随后的讯问中又通过合法方法获取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重复供述。有学者指出:新《刑事诉讼法》及其司法解释对重复供述问题未作出规定,这是关于非法证据的规制中最为突出的问题,也是最为显著的缺漏。[2]
若不认真对待重复供述问题,恐怕设定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良法美意无法达成,程序性制裁机制也将被架空。因此,我们必须认真对待重复供述问题。
一、非法证据排除继续效力的提出
对重复供述问题,目前存在三种应对模式:直接适用非法证据排除规则模式、“毒树之果”模式和证据使用禁止的放射效力模式。这三种模式能否妥善地处理重复供述问题?
(一)直接适用非法证据排除规则模式
如我国台湾地区“最高法院”93年度台上字第6018号判决认为:被告之自白,须非出于强暴、胁迫、利诱、诈欺、违法羁押、疲劳讯问或其他不正之方法。对被告施以上揭不正之方法者,不以负责讯问或制作该自白笔录之人为限,其他第三人亦包括在内,复不以当场适用此等不正之方法为必要,从系由第三人于前此所为,倘使被告精神上受恐怖、压迫之状态延续至应讯时,致不能为任意性之供述时,该自白仍属非任意性之自白,依法自不得采为判断事实之根据。[3]
再如,台湾地区“最高法院”93年度台上字第6578号判决认为:自白系出于不正方法者无证据能力之侵害性法则,并不限于负责讯问之人员对被告为之,即第三人对被告施用不正之方法,亦属之,且不论系事前或讯问当时所为,只要其施用之不正方法,致被告之身体、精神产生压迫、恐怖状态延伸至讯问当时,倘被告因此不能为自由陈述者,其自白仍非出于任意性,不能采为证据。[4]
综上,我国台湾地区“最高法院”的观点是,如果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在侦查人员使用非法讯问方法供述后,并没有脱离其先前所受讯问的心理强制,之后其所作的供述,仍被视为是非法证据,法院将依据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直接予以排除。
但需要注意的是,重复供述并非典型的非法证据。如前所述,重复供述问题讨论的对象是在侦查人员非法讯问获取被告人供述后,在随后的讯问中通过合法方法获取的被告人的重复供述。因此,侦查人员获取第二次供述的取证行为是合法的,该供述不属于典型意义上的非法证据。
在直接适用非法证据排除规则模式的台湾地区,“最高法院”强调的关键点是被告人在侦查人员使用非法讯问方法供述后,有无脱离其先前所受讯问的心理强制。可见,对于“有无脱离先前讯问的心理强制”这一问题,该模式的适用仍需进一步的判断标准,而一旦附加了进一步的判断标准,重复供述的排除就不再那么“直接”了。所以,直接适用非法证据排除规则模式是一个不够独立,操作性较差的模式。
(二)“毒树之果”模式
在应对重复供述问题时,美国主要适用“毒树之果”模式。
“毒树之果”理论以侦查人员非法获取的证据为“毒树”,由该非法证据所派生的证据为“毒果”,不得作为定案根据。换言之,在“毒树之果”模式中,作为侦查人员最初非法行为直接产物的证据应予以排除,作为非法行为的间接产物或派生的证据也应予以排除。美国联邦最高法院在1939年通过Nardone v.U.S案阐述了“毒树之果”理论的法理基础:“如果只对非法获取的证据的直接使用加以禁止,对其间接使用不做抑制,无疑将激励这种与伦理相悖并侵犯公民自由的非法取证方法。”[5]
具体而言,“毒树之果”模式应对重复自白问题又涉及两种具体情形:
一者,是侦查人员第一次自白的获取违反了米兰达规则。在1985年的Oregon v. Elstad案中,联邦最高法院认为米兰达规则是预防性规则,不是公民的宪法性权利;在获得先前的供述时,如果侦查人员没有故意强制或使用其他非法取证手段,仅是没有告知犯罪嫌疑人米兰达规则,而之后犯罪嫌疑人经由告知米兰达规则所作的供述,不应像先前的供述那样被排除。[6]概言之,第一次自白没有证据能力的违法原因在第二次自白时已不复存在,则无理由排除第二次自白。2004年,情况发生了变化。在Missouri v.Seibert案中,在第一次讯问时,侦查人员未告知犯罪嫌疑人米兰达规则,犯罪嫌疑人作出自白;20分钟后,侦查人员告知其米兰达规则,犯罪嫌疑人再次重复了先前的自白内容。美国联邦最高法院的大法官以5:4的票数裁定第二次自白应当被排除。[7]促成这一转变的,有两个背景性事件:其一,Oregon v.Elstad案后,侦查人员在讯问犯罪嫌疑人之前,总是先故意不告知米兰达规则,在犯罪嫌疑人自白后,再告知其相关权利,并重新讯问以取得相同内容的自白。甚至,这一方法还成为了全国性的警察培训机构传授警察的讯问秘籍。[8]其二,联邦最高法院在2000年的Dickersonv.U. S.案中认定,米兰达判决是基于宪法所做成的判决。[9]换言之,米兰达规则所保障的是宪法性权利。
二者,是侦查人员第一次自白的获取违反了自白任意性规定。比如在侦查人员刑讯逼供的情形下,被告人做出了第一次自白,之后,侦查人员遵循正当程序重新讯问,被告人做出了第二次自白。此时,因为第一个自白是侦查人员非法取证的产物,自白无任意性,应予排除;第二个自白前即使告知被告人米兰达规则,仍应适用“毒树之果”,除符合例外规定外,应予排除。美国联邦最高法院在2003年的Chavez v. Martinez案中主张:我们的判例法规则是,遭受强制性警察讯问的个人受到自动保护,以保证他的非任意性自白或者由此所派生的证据不在随后的刑事审判中使用。[10]
但这里需要澄清的是,重复自白并非派生证据。“毒树之果”模式中的核心概念是派生证据,即“因程序瑕疵所获证据,进而发现并合法取得之证据”[11]。而重复自白的情形,美国联邦最高法院曾指出,关于来自同一被告人的先前非法获取的自白的随后的自白之可采性问题,“毒树之果”理论不能得到适用。[12]如在1944年的Lyons v. Oklahoma案中,联邦最高法院认为,第二次自白可采性的判断依据同第一次自白的一样,即自白是否具有任意性;先前的刑讯逼供行为始终强制着被告人的心理,使之在第二次自白时仍然是非任意性的。[13]换言之,美国联邦最高法院在处理该案时,主要依据是第一次自白时的非法取证行为是否对第二次自白产生了心理上的继续强制效力,而非适用“毒树之果”理论。此后,美国联邦最高法院在处理一系列涉及第一次非任意性自白的案件中,关注的问题仍是“是否第二次自白本身是自愿的,而不是询问第二次自白是否是第一次的果实。”[14]可见,在重复自白情形下,第一次自白与第二次自白之间并不存在典型的派生关系,重复自白问题不是派生证据问题。
国内赞同该观点者认为:“毒树之果”中的“果”应当是独立的新证据,而不是原有证据的重复收集。先通过刑讯的方法获取被告人的口供,然后再用合法的讯问方法,让被告人将口供重述一遍,仍然属于非法证据范畴,而不是“毒树之果”。因为实质上,这种情况下该证据还是通过前面的非法取证行为获得的,而不是通过后面的合法方式获取的。[15]简言之,重复供述仍然是“毒树”本身,并不是“毒树之果”。[16]可见,对于重复供述的排除,并不能基于“毒树之果”模式,因为第二次供述与其说是通过第一次供述派生的,毋宁说是先前非法讯问方法对其任意性继续产生的影响。所以,“毒树之果”模式不太契合重复供述情形。
大陆法系国家或地区针对侦查人员非法讯问所获取的被告人供述,设置了证据使用禁止的三种效力范围:直接效力、继续效力和放射效力。[17]其中,在德国刑事诉讼法学上,证据使用禁止的放射效力(Fernwirkung)是指一证据使用禁止之效力亦可深达间接取得之证据上。[18]根据德国通说,该学说处理的问题即是美国“毒树之果”理论所遇到的问题,[19]两者都是为了避免证据使用禁止规则被轻易规避。换言之,两者表述的问题是一致的:侦查人员刑讯逼供获取了被告人供述,再依据该供述合法获取了派生证据,此时,作为原始证据的第一次供述可以被直接排除(直接效力),但是,作为派生证据的第二次供述是否应当排除(放射效力)?
具体到侦查人员非法讯问获取供述的问题,放射效力的意义在于:证据使用禁止必须有放射效力;证据使用禁止的放射效力必须有限制;证据使用禁止的放射效力,因案而异,方法上应以个案中被违反法规的规范目的出发,同时审酌侦查人员主观上(如故意或过失、恶意或善意等)及客观上(如侵害权利之方法、种类及范围等)的违法程度,犯罪嫌疑人涉案程度及所涉案件是否重大等因素。实务中也有适用放射效力模式的司法判例。如德国联邦法院处理的一起案件中,一名潜入牢房的密探向被告人探听到犯罪的始末,侦查人员通过该密探的证言调查出一名证人,并取得该证人的证言。[20]显然,该证人证言属于密探证言的派生证据,控辩双方关于该证言的争论实为关于放射效力的争论。此外,日本学者认为这一争论所强调的是:“前一个程序违法会波及后一个程序(违法侦查的波及效应),从而扩大了违法判断的对象。”[21]葡萄牙学者将这些争论称之为“禁用证据的牵连效应”问题,如葡萄牙最高法院于2004年在第2194/04-5a号卷宗所作出的裁判中认为:“对于所获得的证据因被禁止而不得使用的情况——可延伸至——透过其直接或间接取得的证据亦不能使用。”[22]
但是,与“毒树之果”模式一样,在证据使用禁止的放射效力模式中,其核心概念也是派生证据。而通过上文分析可知,重复供述并非派生证据。可见,证据使用禁止的放射效力模式也不能解决重复供述问题。
通过对现有应对重复供述问题三种模式的分析,我们发现,这三种模式在处理重复供述问题上均有种种弊端,有必要提出另一种新模式。新模式所要处理的核心问题又是什么呢?
众所周知,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供述任意性的保障,涉及到被告人最为根本的程序性主体地位,与被告人的人格尊严不受任何侵犯相关。重复供述问题中,判断先前非法讯问对随后供述的任意性是否继续产生影响成为了问题的关键。而关于该问题,我们可以适用“任意性值得怀疑”标准,即“程序是否正当而且被告人是否自愿值得怀疑”。[23]详言之,如果随后的重复供述均被侦查人员第一次的非法取证行为所“污染”,不仅应排除第二次供述,被告人随后作出的供述均应予以排除。如我国台湾地区“最高法院”87年度台上字第2461号判决认为:被告之自白,倘非出于任意性,则不问该自白内容是否确与事实相符,因其非适法取得之证据,无证据能力,即不得采为判决之基础。又若被告先前受上开不正之方法,精神上受压迫所为非任意性之自白,其所受精神上压迫状态,足证“已延伸至后未受不正之方法”所为之自白时,该后者之自白仍不具有证据能力。[24]再如,台湾地区“最高法院”87年度台上字第3339号判决认为:此项证据能力之限制,系以被告之自白必须出于其自由意志之发动,用以确保自白之真实性,故对被告施以上揭不正之方法者,……倘使被告精神上受恐怖、压迫之“状态延续至应讯时致不能为任意性供述时”,该自白仍属于非任意性之自白,依法自不得采为判断事实之根据。[25]可见,重复供述问题在于先前非法讯问对随后供述的任意性是否继续产生影响。
因此,鉴于现有的三种模式在处理重复供述问题上存在缺陷,有必要提倡一种以处理“先前非法讯问对随后供述的任意性是否继续产生影响”为核心的模式。其基本立场为:在侦查人员第一次非法讯问后,当第二次讯问时,如果第一次讯问对被告人供述任意性的侵害效果继续到了第二次讯问,导致被告人供述时丧失任意性,则第二次供述没有证据能力。德国也有持同样观点的:“即或后来的讯问方法并无违法情事,然其陈述仍受昔往不法之讯问的压力影响时,则此时虽属合法之陈述仍不具证据效力”。[26]
概言之,笔者所提倡的供述继续效力模式具有以下三方面性质:(1)继续效力模式解决的不是典型的非法证据问题;(2)继续效力模式应对的不是派生证据问题;(3)继续效力模式处理的是先前非法讯问对随后供述的任意性继续产生影响的问题。
二、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继续效力的判断标准
我们明确了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继续效力模式,用以处理重复供述,其核心问题是:先前非法讯问对随后供述的任意性是否继续产生影响。那么,如何判断是否继续产生影响,换言之,继续效力之判断标准何在?
美国“毒树之果”理论对派生证据是否受到先前非法行为的污染,并未设置明确的判断标准,而是将这一判断标准委诸规范保护目的与实施成本的个案权衡。[27]德国在证据使用禁止规则的发展过程中,也放弃达成所谓“判断标准通说”的努力,“转而代之的是对不同的利益关系在个案中区别加以分析的个别的举证禁止”。[28]有鉴于此,对于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继续效力之判断,我们也很难设置一个明确的标准,相反,我们只能委诸个案判断。[29]我国台湾地区的实务界亦持此观点:被告人自由意志所受之强制,系来自于侦查人员之不正行为,及该次讯问所处之环境等外在因素所致,除非妨碍被告人意思自由之外在因素消失,受讯问人之意思自由自随之回复外,否则,判断受讯问人所受之强制是否已延续至其后之应讯时,仍应研究该次不正方法与嗣后之自白间之相关联因素,包括讯问时间是否接近,讯问地点及实施之人是否相同,受讯问人自白时之态度是否自然,陈述是否流畅等,以定其因果联系之存否。[30]因此,关于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继续效力,我们应当综合案件事实加以具体判断,权衡被告人被讯问时的每一个因素,包括:侦查人员非法讯问时的客观违法形态与主观违法情形,以及讯问主体有无明显变化,讯问情势有无实质变更,有无中断先前非法讯问影响的事实介入,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是否深信其第一次自白仍然继续有效等。
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继续效力的个案权衡,首先要考察侦查人员非法讯问时的客观违法形态。与较为模糊的主观标准相比,客观违法形态更易识别,即反映了侦查人员“偏离法定要求的程序以及是否该偏离系以一种使其对被告产生特别严重的影响的方式出现的”[31]多种违法形态,如刑讯逼供、威胁、引诱、欺骗、违反法定告知义务。美国联邦最高法院在1975年的Brown v. Illinois案中主张:先前违法行为越恶劣,派生证据受到的污染就越难以洗清。[32]英国证据排除规则中的“保护原则”,其相关因素也包括侦查人员侵权行为的严重性,以及对被告人产生的影响。[33]
(二)侦查人员非法讯问时的主观违法情形
侦查人员非法讯问时的主观违法情形,主要是看侦查人员先前行为系故意抑或过失、恶意抑或善意,即考量侦查人员“受获得归罪性承认的愿望所激发的程度。”[34]如美国联邦最高法院在1984年的 U. S.v. Leon案中创设的“善意例外”(the good faith exception):如果非法搜索的侦查人员客观合理地相信搜索票有效,侦查程序合法,那么其取得的证据不应排除。[35]其法理基础在于,该案即使排除了相应证据,从抑制侦查人员非法取证的规范保护目的看,也不会起到抑制非法取证的吓阻效果。再如我国台湾地区“刑事诉讼法”第158条之2第1款规定,经证明警察违背程序非出于恶意,且该自白或陈述系出于自由意志,其所取得的被告或犯罪嫌疑人之自白及其他不利之陈述,仍得作为证据。
可见,如若侦查人员先前违反取证程序的行为是善意的,即获取供述的侦查人员没有故意藐视被告人的合法权益,而是过失或错误地相信自己的行为是合法的,则其获取的重复供述的证据能力存在讨论空间。
(三)稀释的程度
非法证据排除模式的继续效力模式虽与“毒树之果”理论和证据使用禁止的放射效力模式存在显著差异,但在个案权衡上仍可以从作为“毒树之果”理论例外的“稀释规则”(the purged taint exception)[36]中汲取经验。稀释规则,是指在侦查人员第一次非法取证后,第二次合法取证前,存在其他独立因素的介入,足以稀释或涤除先前非法取证行为的违法性污点,此时,该证据可以例外地具有可采性。美国联邦最高法院在1939年的Nardonev.U.S.案中主张:如果侦查人员的非法取证行为与争议证据之间的关联性已经变得微弱得足以洗涤先前的污点,那么侦查人员非法取证行为所获得的证据具有可采性。[37]其法理依据为:“净化受到的污染这一概念试图确定一个界定点:据此,警察违法行为的危害性已经变得如此微弱,以至于排除规则的威慑作用已经小于所付出的成本”。[38]1963年的Wong Sun v.U.S.案确立了至今适用的判断标准:是否存在足以稀释先前非法取证行为所造成污染的明显不同的其他取证手段。[39]详言之,稀释规则包括以下三个方面:
1.讯问主体有无明显变化,讯问情势有无实质变更
一般而言,如果被告人在侦查人员第一次讯问时,因刑讯逼供而供述,即使侦查人员第二次讯问没有再刑讯,但在讯问主体和讯问情势尚未发生实质变化的情况下,我们仍然不可能期待被告人不受先前刑讯逼供的影响,此时,被告人重复供述的任意性仍存疑问。
需要注意的是,即使讯问主体发生变化,仍应对讯问情势进行具体判断,如被告人在侦查阶段因刑讯逼供而供述,侦查人员威胁其不得在审查起诉阶段向检察官翻供,因此,即使之后检察官在讯问时并未使用非法讯问方法,但因先前的刑讯逼供对被告人供述的任意性继续产生影响,讯问情势没有实质变更,其重复供述仍应予以排除。日本最高法院的判决认为:第一次自白是向警察作出的,第二次自白是在法官逮捕质问时作出的,决定逮捕时进行的质问是由侦查人员以外的其他独立机关,即法官实施的,而且在决定逮捕质问程序上给犯罪嫌疑人辩解的机会,因此逮捕质问笔录具有证据能力。[40]随后,日本有些下级法院否定了这种逮捕质问笔录的证据能力,其判断标准是看被告人在逮捕质问中所作的自白是否被第一次自白时讯问的违法性所波及,比如重复自白若与第一次自白的内容完全一致就应当予以排除。我国司法实务界有观点认为:“如果到了法庭上,被告人面对法庭还继续作有罪供述,这个证据就可以采用了,因为法庭环境不一样。如果在法庭上被告人作无罪供述,又确实有证据能够证明此前的有罪供述系刑讯逼供,庭前相关有罪供述就一律不能用。”[41]概言之,该种观点认为,除了讯问情势已有实质变更,只要有一次能够证明是刑讯逼供获取的供述,之后的重复供述就一律不得使用。
“讯问间隔的时间”是判断讯问情势有无实质变更的另一重要标准,这一标准要求审酌重复供述与先前非法讯问行为之间的间隔时间是否紧凑。详言之,“最初的违法行为与取得证据——该证据的可采性后来受到了质疑——之间的时间间隔越短,法院就越有可能得出以下结论,即该证据已经受到了污染”。[42]美国联邦最高法院在2000年的Dickerson v. U. S.案中主张,在犯罪嫌疑人作出第二次自白前,侦查人员需要就第一次讯问的瑕疵,采取必要的“治愈措施”,否则第二次自白应当排除。这里的“治愈措施”包括两次讯问之间存在显著的时间间隔或者存在显著的情势变更。[43]
此外,我国台湾地区的判例也有持此观点者,如“高等法院高雄分院”刑事判决92年度上更(一)字第299号判决认为:被告第二次警讯自白贩卖毒品,已距第一次警讯前遭非法逮捕达16小时;再者,被告第二次警讯笔录制作时连续录音,被告回答之声音清楚连贯,笔录所载内容亦与被告所述相符。足见被告在第二次自白时不仅距非法逮捕之时间已久,且系因施用毒品案件证据明确而等待移送检察官,又依上开连续警讯录音带勘验结果,被告并未经警方以其他不正之方式取得自白,则本件警方违反人权保障(违法逮捕)之瑕疵已经稀释。[44]该案中,讯问情势已有实质变更:其一,讯问时间间隔较长,时间已然成为最好的解药;其二,第二次讯问有连续录音加以印证,且笔录与录音相符。再如,台湾地区“最高法院”97年度台上字第3344号判决认为;蔡某于原审已证称其于调查站讯问后,接继由检察官在调查站内为复讯,且复讯时原讯问之调查员仍站立在旁。所称如果无讹,蔡某所受调查员不正方法所致自由意志之受强制,于检察官复讯时其外在之影响因素是否已消失?原讯问之调查员仍站立在检察官旁,是否仍影响蔡某之自由意志?原判决……并未调查审认检察官于复讯时,原施以不正方法为讯问之调查员是否确实站立在旁?此种情形是否已影响及蔡某之自白系出于自由意志?攸关蔡某于检察官讯问时之陈述有无证据能力。[45]该案的讯问情势即属尚未发生实质变更:其一,两次讯问的间隔很小,接连发生;其二,第二次讯问时原讯问的侦查人员仍在现场,导致蔡某所受侦查人员先前非法讯问方法的心理强制尚未被稀释,重复自白的任意性仍存疑问。
2.有无中断先前非法讯问影响的事实介入
我国台湾地区“最高法院”101年度台上字第5570号判决认为:非任意性自白之继续效力,须视第二次自白能否隔绝第一次自白之影响不受其污染而定,亦即以第一次自白之不正方法为因,第二次自白为果,倘两者具有因果关系,则第二次自白应予排除,否则,即具有证据能力。[46]换言之,该判决认为如果前后两次自白之间介入稀释先前非法讯问污染的事实,则因果关系中断,继续效力不复存在。接下来的问题是:侦查人员先前非法讯问与所欲判定的重复自白之间,介入什么事实或介入多少事实可以中断其对随后自白的任意性继续产生影响?有学者认为,这属于“多次性派生证据”问题,类此树生果,果又生树,树又生果的情形,对证据使用禁止效力的判断应予以限制,进而主张该效力不及于再派生证据。[47]换言之,证据使用禁止效力原则上仅及于第一次派生证据,不及于因派生证据合法取得的再派生证据。而此标准仅以派生次数为限,并无判断是否继续产生影响的实质标准,过于注重形式,在重复供述问题上几无运用空间。
但不容否认的是,先前非法取证行为与被质疑的证据之间介入的事实越多,该证据就越有可能具有证据能力。换言之,“当在被质疑证据和先前的非法行为之间的联系足够长或者该联系仅仅通过复杂的争论才能够被显示时,排除显得不合适”。[48]其正当化事由是:“由于事件之间的因果关系链条变得很长,警察不太可能预见到受到质疑的证据会被认定为非法行为的产物,因此,排除规则的威慑作用也就被大大削弱了”。[49]还有学者指出:“嫌疑人被解送至治安法官前并被该法官忠告,这倾向于表明稀释;另一方面,如果介入事件由讯问和其他的警务行为构成,而这些行为系采用了拘禁并意在利用该拘禁来说服被告作出归罪性陈述的话,显然这些介入事件显示了稀释尚未发生。”[50]
司法实务观点方面,美国联邦最高法院在1963年通过Wong Sun v. U. S.案确立了“稀释规则”:第二个证据若是利用非法方法获取的原始证据的产物,则应(适用“毒树之果”理论)予以排除。但是,如果有充足的理由可以辨识原始证据的污点已被稀释,则(作为“毒树之果”理论的例外)无须再行排除。[51]该案中,Wong Sun作了两次供述,第一次供述是在被侦查人员非法逮捕后作出的,第二次供述是在交纳保释金被释放数日后,自愿返回警察局向侦查人员作出的。联邦最高法院的大法官认为这些事实足以稀释先前非法逮捕的污点,非法逮捕对第二次自白的影响已近消弭。概言之,该案存在被告人自愿行为的介入,进而中断了先前非法取证行为所造成的污染。台湾地区“最高法院”93年度台上字第6656号判决认为:调查员以不正方法取供后,检察官又对其进行了两次讯问。上诉人于检察官侦查中之初供,距其于调查局讯问时之陈述已逾一个月又十日,又其第二次在检察官侦查中之供述,并有选任之辩护人到庭执行职务,……足证上诉人先前因上开不正之方法,所受精神上之压迫状态,并未延伸至其后未受不正方法所为之自白。[52]
3.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是否深信其第一次供述仍然有效
重复供述问题中,我们若要准确判断先前非法讯问的“污染”是否已被“稀释”,必须首先明了一个事实:“一个人被说服,暂时或一直承认自己有罪,或者被骗后,沮丧地认为没人相信自己,为了避免再次受到讯问而把所有的事都承认了下来,都会做出虚假的供认。”[53]因为根据司法心理学的研究成果,在被羁押讯问时,存在一种不可避免的压力导致被告人认罪。这种压力可能是因为羁押和讯问、心理脆弱性或是各项因素的结合。当被告人存在内在的压力和动机而非仅有外在压力去“回想”所谓的犯罪事实时,他们更可能去相信自己卷入到了案件中或是伤害到了被害人,即伴随着“错误的信念”产生了“错误的记忆”。[54]换言之,一旦被告人深信第一次供述仍然有效,案件已有定论,在随后的讯问中他别无选择,只能继续重复其已作出的供述,因此,先前非法讯问所造成的违法性“污染”将持续下去,而未得到“稀释”。
在美国联邦最高法院1985年审理的Oregon v.Elstad案中,辩方提出了“覆水难收”论(let the cat out of the bag theory):一旦被告人在先前的非法讯问中作出了自白,已经形成了对其心理的强制,因为一般人都会觉得先前都已经承认了,再保持沉默已无意义。[55]换言之,被告人认为自己既已自白,已经露了底,覆水已然难收,就如同让猫跳出口袋后,再也抓不回来一样。美国联邦最高法院在2000年的Dickerson v.U.S.案中提出的“治愈措施”还包括,侦查人员在第二次讯问前,应向被告人告知其第一次自白不具有可采性,从而使被告人无需顾虑其已露底,覆水难收。这两个判例说明,如果治安法官、侦查人员或者辩护律师告知被告人先前的供述是非法获取的,无论其本身抑或其所派生的证据都不能用,此时,便会稀释先前非法取证行为对随后证据的污染。[56]
上述“覆水难收”理论的要义为:被告人往往认为,其既已为第一次自白,并深信该自白仍然有效,因而其再为第二次自白,对其已别无所失且别无选择。因此,前后两次自白之间,关联紧密,因果关系尚未中断。在大陆法系国家和地区,该问题被转化为:随后的侦查人员应否向被告人践行加重的告知义务?详言之,针对在先前的讯问中,侦查人员未尽告知被告人沉默权的义务,而在随后的讯问中经被告知沉默权后,被告人仍为重复自白这一情形,关于其随后的重复自白应否具有证据能力,德国司法界和学术界的观点为“加重的告示义务”说,即看随后的讯问中被告人是否在被告知沉默权的同时,还被告知其之前所为的供述并没有证据能力。[57]
(未完)
出处:《法学家》2015年第2期 作者:吉冠浩

台湾A公司,2003年在深圳注册,长期生产电子元器件,各类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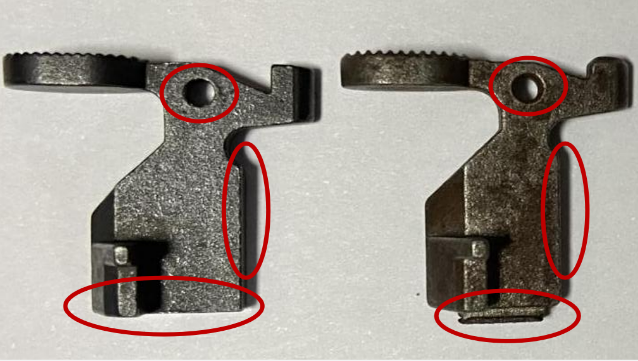
L为H公司的总经理及实际经营者。H公司为Z公司的合作公司,从
程先华律师近年来接手许多合同诈骗罪类案件,而诈骗名目有民族资

近年来,互联网销售的便利,仿真枪在我国市场上流通越发增多。伴

伙年轻人包厢唱歌因口角而发生打斗,后陆续去医院处理伤口。不料